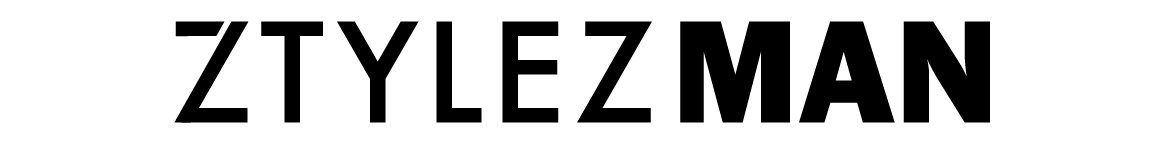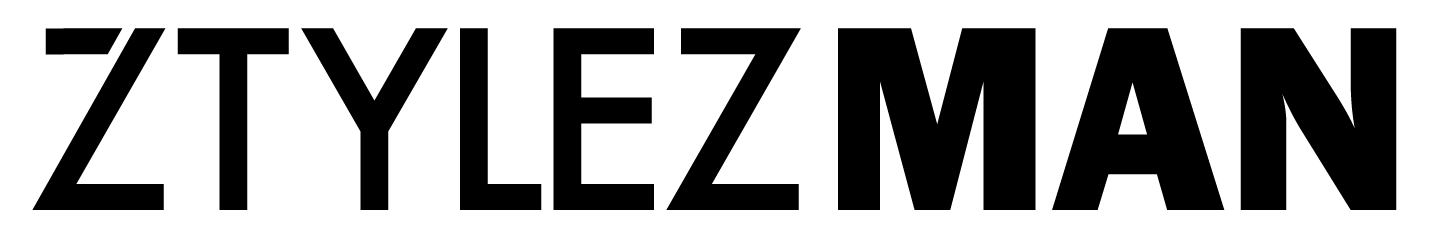近期,特朗普政府因對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處理去年親巴勒斯坦抗議的反應,決定取消對該校4億美元的撥款及合同。聯邦政府向大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暫停或開除參與抗議的學生,而哥倫比亞大學則表示願意遵從這些要求。
截至目前,撥款仍被扣留,聯邦專案小組指出,哥倫比亞的讓步僅僅是”第一步”。這使得該校的數十個醫療及科學研究項目陷入停滯,健康及人類服務部並未對相關查詢作出回應。
同時,哥倫比亞大學亦面臨越來越多的批評,許多反對者認為該校應該動用其雄厚的捐款基金來彌補政府撥款的短缺,而非屈服於壓力。根據《全國高校商務官協會》及資產管理公司Commonfund的研究,哥倫比亞大學的捐款基金達148億美元,是美國第12大高等院校捐款基金。
該研究顯示,658所院校的捐款基金總額達8737億美元,但財富高度集中,86%的資金由五分之一的學校所掌控。儘管哥倫比亞大學的捐款基金規模相對較大,但鑒於該校的學生人數較少,平均每位學生的捐款基金約為50萬美元,這一數字遠高於德克薩斯大學的不到25萬美元。
然而,較富裕院校的捐款基金中,部分資金為流動性較差的資產。哥倫比亞的捐款基金中,全球股票佔31%,而私募股權及實物資產分別佔26%和12%。固定收益及現金佔2%及1%,剩餘的28%則分配給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絕對收益策略基金,這部分資金同樣具備流動性風險。
教育歷史學家布魯斯·金博爾(Bruce Kimball)認為,許多大學之所以能集中如此財富,與其願意投資於風險較高的資產密切相關。過去,大學捐款基金的投資策略相對保守,但是隨著哈佛在1951年大膽調整其資產配置至60%股票和40%債券,其他院校也逐步跟進。在1990年代,耶魯大學開始投資對沖基金和自然資源,這一”耶魯模式”的成功使得只有擁有較大捐款基金的學校才能承擔這類風險。
捐款基金實際上並非隨意可用的資金,學校的捐款基金由數百甚至幾千個基金組成,其中多數由捐贈者限制使用,通常用於教職員工、獎學金或研究等特定領域。舊金山大學的前主席斯科特·博克(Scott Bok)指出,大學並無法隨意動用這些資金。根據經濟學家的說法,大學通常只按照每年5%的比例支出捐款基金,使本金能夠長期增值以抵禦通脹。
科學家兼前西北大學校長莫頓·沙皮羅(Morton Schapiro)指出,在危機時期,增加捐款支出是可行的,許多學校在疫情期間便做到了這一點。捐款者也可以書面同意解除捐款限制。對於大學而言,捐款基金的支出有重要意義,但若將捐款基金用於短期支出,可能會影響未來的資金流動。透過其他途徑爭取撥款或許會更具挑戰性,尤其是當大學面臨著重大的財政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哥倫比亞大學能否妥善解決資金問題還有待觀察。當前,國家衛生研究院正實施間接成本的15%上限,導致研究經費的進一步壓縮。此外,一些國會議員提出增稅方案,這可能增加對於某些院校的壓力。隨著國際學生的減少,更多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隨之而來。
No tags for this post.